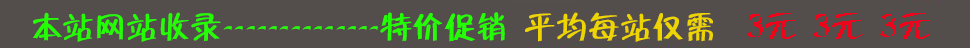許多互聯網弄潮兒喜歡用標簽勾勒自己的線上形象,再把諸多概括類名詞用一個個豎杠區隔開來。我時常想象,如果這些標簽能夠實體化,應該會幻化為別在他們胸前的“徽章”。
畢業院校、學歷程度、任職經歷是人手一枚的標配款;除此之外,也有與時俱進的流行款。這些流行款曾經是“幣圈人士”“Web3創業者”“DAO成員”,如今則是“一人公司”。
于是,我意識到,新的風向出現了。
2012年,Instagram 以10億美元賣給 Facebook 的時候只有13名員工,大眾均對此表示難以置信;
2022年,一家名為 BuiltWith 的網站年入超1億元時,公司只有開發者 Gary Brewer 一人,國內網友很快將其奉為“創業大神”;
2024年,短短兩年過去,OpenAI 的首席執行官 Sam Altman 已經開始期待,能夠達到10億美元估值的 “一人公司” 將在何時誕生。
一小部分人開始接受并相信。
當技術的迭代周期以指數級加速, AI Agent 能夠以更強的易用性滿足更多樣的生產需求,也許“越來越小的體量,越來越大的價值”才是未來“公司”的模樣。
更小的一部分人開始踐行,以個體作為最小單元,在直面社會中謀求生存與個人成長。
盡管他們中間的許多,并沒有實際注冊屬于自己一人的公司,但“一人公司”所象征的“像經營一家公司那樣經營自己”的理念,正指引著他們的行動。
一場“出走”
工作日下午兩點,北京朝陽某家書店的咖啡區,坐著不少人。
從鍵盤上飛舞的指尖,屏幕上層疊的聊天框,以及快要見底的咖啡和凌亂的桌面來看,他們當天已經在這里坐很久了。
歪歪起身迎接我,她的座位在咖啡區中央一條能容納8人的長桌上。在之前的線上聊天中,她將這里稱為“我們咖啡館”,這并不是說咖啡館為歪歪所有,而是指她會和其他的自由職業者朋友,固定在這里辦公。
2022年夏天,歪歪從一家自媒體機構裸辭,選擇成為一名“ IP 孵化手”,給有打造個人IP需求的老板們提供賬號代運營服務。她自己找客戶,自己交付服務,就像一家只有一個人的小型公司那樣。
為了緩解獨自奮斗的孤獨,歪歪與坐在對面的瑪莎結成了創業搭子:“她很厲害,已經年入近百萬了。”
瑪莎,85后,自小學畫,兒時夢想是成為油畫家,“后來發現還沒當上就得餓死”,遂放棄。大學修的是設計專業,畢業后先做品牌全案設計,后又做了14年的 UX 設計師,一路從普通小職員做到公司設計總監。
在2022年6月之前,瑪莎的人生一直按照大眾眼中的“標準劇本”進行,然而,當她已經在公司做到了設計總監,反而選擇了離開。
“上班跟上墳一個邏輯,光上班也還行,但能不能干點正經事?!?br />
情緒在公司要求她裁掉組員時開始累積。行情好,公司搞賽馬制,設兩個總監兩個團隊;行情不好,需要降本,瑪莎將自己的團隊裁到只剩5人,公司還要再裁。每天忙到晚上10、11點才下班,大家都走了,瑪莎會站在樓頂思考。
“不是想跳下去哈,我挺樂觀的,就是思考一下未來?!币娢衣冻鰮鷳n的表情,瑪莎連忙解釋。
情緒在一個夜晚集中爆發?,斏谏钜?2點回到家,走進臥室時,看見3歲的女兒騰地坐起來,問:“媽媽是你回來了嗎?”瑪莎詢問女兒為何還不睡覺,女兒說:“媽媽我在等著你抱抱我。白天見不到你,晚上還是見不到你?!?br />
瑪莎并不是會因此就在家相夫教子的性格,但在公司花費大量時間,卻無法做自己認為更有意義的事情,這種感覺讓她難以忍受。第二天,她找領導要了一個裁員指標,自己拿著n+1,瞞著所有人交了11萬8的創業課程學費。
無論歪歪還是瑪莎,經常會提到的一個詞是“出來”,她們會把截止到目前的人生劃分成“出來之前”和“出來之后”。
歪歪是95后,性格開朗,愛笑,985大學畢業,憑借高分就讀搶手的經濟管理專業,是會被父母們夸贊的“鄰居家的小孩兒”。
但她告訴我:“讀經濟管理專業只是因為高考分數高,不想浪費分數,自己并不喜歡?!焙芸欤鸵庾R到:不喜歡的事情,怎么也做不好?!皩嵙暤臅r候去審計公司工作,天天寫報表、分析資產盤,沒有任何熱情?!?br />
“出來”,用來代稱走出職場的同時,似乎也隱含了幾分跳出既往框架和標準的意味。
在見到歪歪與瑪莎的前一天,我還順著網線聯系到了一位正在獨立開發AI項目的程序員 LK。
他與瑪莎一樣是85后,迄今做了將近15年的技術工作,4年 iOS、4年 Android、4年服務器、2兩年前端,身經百戰。
LK 今年剛過35歲生日,即便工作能力強、收入高且穩定,也沒能逃脫程序員的35歲焦慮。從去年開始,他就頻繁地思考:“35歲之后,憑借自己的技術進行工作的合理方式是什么?”
22歲,大學剛畢業時,LK 沒有選擇步入職場,而是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與朋友一起創業。失敗后,他前往北京的互聯網大廠工作,一路安穩地走到現在。盡管中間也曾嘗試過幾回O2O、區塊鏈的小型創業,但都沒有激起太大水花。
直到真正快要走到35歲的關口,這個傳說中充斥著“危機”與“被丟棄”的年齡,LK 還是決定認真地再試一次。去年,他注冊了自己的公司:“覺得這個階段,自己無論是在思想還是技術上都相對成熟了,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?!?br />
目前 LK 還沒有放棄在大廠里的工作,他計劃等自己的小公司能夠覆蓋正職的全部收入時,再離開,可他的生活作息已經因此而改變。
下班后的空余時間,LK 全部用來開發AI項目,就連之前妻子懷孕的時候,每天陪伴妻子到晚上10點多,等她睡了還是會再到書桌旁工作。
他并不排斥上班,但做自己的項目,顯然更有吸引力。
嶄新且復雜的地圖在每一個“出走”的人面前展開,隨之而來的問題是,離開了公司、平臺這類結構性組織,一個人,單槍匹馬,如何界定自己的位置。
給自己加杠桿
很多人的社交簡介上寫著“一人公司X年”,現實里卻不會直接說“我在做一人公司”。
這是因為,大部分將其作為標簽的人,并沒有真正注冊一家企業。
但你也無法因此判定他們不是“一人公司”的踐行者,因為他們確實一人包攬了提供產品或服務、尋找客戶、與客戶談判、簽訂協議、交付并收款等全環節。
在最近的互聯網語境里,“一人公司”象征的不只是一家客觀存在的實體,更是一種理念——個體致力于用最低的經濟成本,提供小而美的產品或服務,用靈活的辦公方式,創造跟一家企業等同的價值與回報。
由于“一人公司”的踐行者與“數字游民”群體有著高度的重合性,我們不妨用數字游民群體的統計數據來了解一些背景。
根據相關報道,2020年以來數字游民的數量增加了三倍,目前全球的數字游民數量超3500萬,預計在2030年將達到6000萬,數字游民的平均年齡是32歲,正逐漸接近人類壽命的中位數。
當在互聯網經濟大潮中成長、學習、工作過的幾代人成為世界的主要生產力,新一代的“打工人”無疑更懂得如何利用時代賦予的工具。
“AI 給個體的能力加了杠桿?!?br />
Cellinlab 語氣興奮,在他看來,有了AI技術的賦能,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“超級個體”。
這位曾經向往做 Web3創業、組建 DAO 的年輕人,2019年畢業后歷經裁員、派系斗爭、創業公司倒閉,正狂熱地相信:“AI 推動生產力升級后,以往獨自一人很難做的的事情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靠AI彌補。個體將有機會脫離傳統的雇傭關系,以更低的成本直接與市場進行交易?!?br />
同為程序員的 LK 最開始沒想這么多。
2023年2月,LK 發現盡管 AI 領域的技術突破如雨后春筍:OpenAI 旗下的ChatGPT 通過了美國醫療執照考試;谷歌推出聊天機器人 Bard;微軟將 ChatGPT整合進 Bing 搜索引擎;Meta 宣布開發 LLaMA 大模型。
然而,國內還有許多用戶接觸不到這些生產力工具,LK 便和朋友們開發了一款名為 HalfWork 的網站,接入了國外幾家成熟的 AI 大模型。當時還沒有“多模態”,他們試著將這些模型整合進一個對話列表中,幫助用戶在對話的場景中調用多種 AI 模型。
圖片
LK開發的AI網站丨圖源受訪者
開發了20天后,網站上線,乘著 AI 的流量東風,網站的日均瀏覽很快破千,積累起了十幾萬用戶,每月收益有兩萬元左右。
但單純依靠自然流量,網站很難持續運營,眼看著 C 端流量逐月減少,去年8月,LK 決定轉向B端產品,為企業做 AI 系統定制。
這次,他又花費3個月獨自完成了面向 B 端的 AI 網站 HalfDone,并注冊了一家名為“事半科技”的公司,正式開啟了一人公司的運作。
從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,LK 一直在社交平臺上更新自己的項目開發進度,即便有了 HalfDone 做基礎,從收到客戶需求到交付,LK 至少要花費一到兩周的時間,但客單價很快提升到了50-100萬元。
很多獨立開發者會把產品發在社媒上進行宣傳,收獲第一批種子用戶;之后一邊迭代產品,一邊通過分享自身創業經驗吸納粉絲,產品最終會慢慢做起來。
LK 認為自己并不擅長做流量,過去十幾年的工作慣性讓他寧愿寫3小時代碼,也不愿寫半小時文章。不得不為網站撰寫相關文案時,LK 會求助ChatGPT,但他從不用AI寫代碼,覺得“AI寫得還沒自己寫的熟練呢”。
他在社交平臺的ID是“AI創業紀實”,一個很難吸粉的名字;因為實在寫不出長篇大論,每篇內容都是簡單的開發進度截圖加日報式的簡短文字。好在,LK 做的是 toB 的生意,對流量、粉絲的需求并不高。
圖片
LK的開發日記丨圖源受訪者小紅書
然而,對依賴線上獲客的人來說,相比起 AI 這類技術工具,“流量”才是他們用來擴展影響力的更重要的杠桿。
凱文·凱利曾在《技術元素》里提出“1000個鐵桿粉絲理論”,意思是“如果你擁有1000個愿意花一天工資購買你產品的鐵桿粉絲,就可以衣食無憂?!?br />
這也是最近“個人 IP”賽道愈發火熱的緣由。
瑪莎告訴我,個人 IP 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做一件去中心化的事情。
大家越來越不喜歡組織化、模式化,越來越傾向于在更細分的領域里找到喜歡的博主,在小圈子里獲得更多的價值感、歸屬感,并愿意為此付費。只要影響力足夠大,或粉絲粘性足夠強,個體也能達到一家小型公司的營收。
一直在幫不同人士孵化 IP 的歪歪同樣認為:“IP幾乎屬于零成本投入,只需要付出時間,流量會像杠桿那樣幫你撬動更大的生意?!?br />
總之,無論是借助 AI 、流量、還是 IP ,意識到傳統雇傭關系的種種問題后,“一人公司”的踐行們,試圖把自己活成一家公司。
六邊形戰士or獨臂戰士
北五環附近的一家民營企業辦公室內,歪歪正“以一敵五”。
早期依靠朋友推薦的客戶資源快要耗盡,她不得不自己外出開拓新客戶。
歪歪將這家民營企業的風格描述為,“在村里的辦公室放張老板椅,老板坐下就開始喝茶那種”。為了拿下客戶,她提前準備好了講解文檔,想跟老板介紹下賬號定位、后期規劃等問題,但硬著頭皮到了之后發現,當天只有自己一個人帶了電腦。
原本要見的民營老板又叫了另外五六個老板一起,他們一邊喝茶,一邊抽煙、侃大山,沒人關心歪歪要講些什么。
“我一個人面對著五六個男性老板,坐在那里還是笑瞇瞇的,但整個人都是緊繃的,腿已經僵了,鼻子里還在吸著二手煙?!?br />
如何把自己推銷出去,是初出茅廬的“一人企業家”們需要學習的第一課,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天生的銷售。
在歪歪看來,做“一人公司”的好處是,你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了。
“在公司打工,老板談來的合作、老板指定的選題,你沒有辦法 say no,但是出來之后,遇到不喜歡的合作者,你可以拒絕?!?br />
但自由的前提永遠是,能夠找到足夠多、足夠穩定的客戶供自己篩選,不然連存活都成問題。公司有自己的銷售、有自己的市場部,自成一家公司后,營收的壓力不會等你做好準備才襲來。
離開職場的第二年,去年年底,兩個老客戶同時與歪歪中止合作,拓客壓力變大,收入變得被動。IP孵化手不再是一個嶄新的賽道,競爭逐漸加大:“很多生意靠的是時間差和信息差,這些不見了之后,該怎么辦?”
一向情緒穩定的 LK,也是在今年3月,三個項目同時不了了之后,開始出現心理波動。
因為要給企業提供定制的 AI 系統,LK 與客戶的合作模式通常是先收一筆小錢做個定制方案或 demo 給對方看,如果對方覺得可以推進,再收幾十萬元開發完整的產品。
“試錯和調整的過程挺痛苦的,三個項目到最后都沒成,付出了很多時間,但沒有結果?!?br />
在現有的一些資料里,人們會把“一人公司”的優勢總結為:“能夠迅速行動,更快地實驗,執行數據驅動的決策,并通過一系列不同的假設進行測試,從而實現產品與市場的匹配?!钡珎€體在其中所需付出的“時間成本”被大大低估了。
由于 LK 同時在做一份正職工作,因此當多個項目并行時,每天晚上7點下班后,他需要繼續為自己工作到凌晨四五點,周末兩個全天也得保持工作狀態。
自己做產品不像在公司里做產品,會有產品經理設計需求、設計師設計UI界面、技術開發完成后還有專門的人負責產品測試。LK 只能有了大體想法后,先參考成熟產品的做法,再在操作中逐漸捋清每個環節。
成為“一人企業家”似乎在逼迫著個體進化為無所不能的“六邊形戰士”,作為旁觀者的我看來,某種程度上這比給公司打工更累,對于個體的考驗更多。
瑪莎卻覺得,作為個體來說,除了選擇當六邊形戰士,也可以做獨臂戰士。“就像現在的 IP 聯合一樣,每個人把自己擅長的東西做到極致,再彼此互補,也可以發揮極大的效果?!?br />
我暗自心想,瑪莎跟 Cellinlab 應該能成為朋友。
在判斷 AI 能夠給個體帶去前所未有的機會后,Cellinlab 也曾想成為一名獨立開發者,但考慮到 AI 產品研發周期長、變現難,再加上對自己更擅長做流量的判斷,他決定走第二條道路——成立 AI 社區,做一名“超級鏈接者”。
“AI 確實給每個人加了杠桿,但 AI 并沒有強到可以幫人做完所有事?,F狀是很多人的技能或資源還在閑置,理想狀態是大家可以分布式協作,共同創新?!?br />
Cellinlab 花了很多時間向我介紹他的“超級個體增長飛輪”項目。
簡單來說,他想做的是把擁有開發、運營、銷售等專長,并且對 AI 感興趣,想要創造 AI 產品的個體鏈接在一起,大家共創產品或服務。而作為“中介”的他,未來將通過從產品收益中抽成的方式獲利,用 Cellinlab 的話來講,這是一種以技術資本進行投資的新模式。
最近,每周二、三、四、六的晚上,Cellinlab 都會直播兩到三小時,邀請嘉賓分享 AI 創業的經驗與思考。每周六,他們還會組織線下的 AI 活動,鼓勵大家分享有關 AI 項目的好點子。
線下活動的場地是位于北京西城區的“昆侖巢”,創始人是曾經創辦“車庫咖啡”的蘇菂。
經歷過十幾年前互聯網創業熱潮,或是了解這段過往的人會知道,位于北京海淀西大街48號的車庫咖啡,是國內第一個以創業為主題的咖啡館,乘著互聯網經濟的東風,不少年輕人曾聚集在這里聊想法、聊技術、組團隊、談投資。
2023年11月,蘇菂又創辦了昆侖巢,希望繼續為有想法的年輕人提供交流場地。自“AI 革命”以來,一顆顆不甘心做一輩子打工人的心臟,再次蠢蠢欲動,大量的線下沙龍、黑松客活動變得愈發頻繁,一批熱血青年正再一次聚集。
能賺錢嗎?
去年,普華永道進行了一項名為“2023年希望與恐懼:全球勞動力調查”的研究。
他們調查了全球46個國家及地區的近5.4萬名員工對待工作的態度及行為,發現,有53%的員工對于目前的職位有所不滿并打算更換工作,即便是打算留在原崗位的人中,也有43%的人并不滿意當下的工作。
關注商業科技領域的作家伯納德·馬爾,認為傳統的工作等級制度正在被動搖,關于“我們的同事是誰”的傳統觀念,將在2024年之后消失。
對于已經在踐行全新工作樣態的人來說,上述論斷是一種“佐證”;可是對于仍在原有軌道上前進的旁觀者看來,上述數據大概率是與自己無關的,非常遙遠的未來。
Cellinlab 一直保留著闡明自己最初想法的帖子,標題里赫然寫著“準備 All in 獨立開發者布道”,內容講解了自己打算激勵更多的程序員轉行“獨立開發者”,再通過將大家聚集在一起從而創造更大的價值。
圖片
Cellinlab最早發布的帖子丨圖源受訪者
評論區熱鬧歸熱鬧,有一大半都在罵他。有人不理解什么是“布道”,有人認為“動不動就套用些大詞、概念的人,跟賣 AI 課程割韭菜的網紅沒有差別”,有人的只留下直白的兩個字——“騙子”或是“圈錢”。
許多人衡量“一人公司”到底是切實可行的新路徑,還是被鼓吹起來用于收割普通人的偽概念,簡單粗暴的標準都是“錢”。
“有沒有賺到錢?”“賺了多少錢?”自從離開公司自己單干后,歪歪的親戚經常旁敲側擊地提出這些問題。
“他們會認為你做‘一人公司’很賺錢,可能已經大賺了一筆,不然做這個事情干嘛呢?”
反過來看,一些網友質疑 Cellinlab 的原因無非也是覺得這個人“在立人設騙錢,什么對于 AI 超級個體的信仰,都是噱頭”。
我厚著臉皮問 Cellinlab,所以這四個月你靠做 AI 社區到底賺到錢沒有?
他答:自己的 Twitter 賬號做起來之后接過一些投放需求,賺了幾百塊,但如果算上為社群付出的人力成本,收入得是 -1萬。
吊詭的點在于,當你知道他沒有因此獲利時,第一反應并不是認為他洗脫了是騙子的嫌疑,而是“原來做一人公司也沒那么賺錢嘛”。
的確不是每個人都能像瑪莎或 LK 那樣“賺一筆”。
離開職場兩年間,瑪莎成立了星火集·設計職業發展研習社,作為一名職業導師為學員做職業規劃。創業第一年,她就賺到了70萬,創業第二年,年收入正接近百萬。LK出售的 AI 系統,定價就在50到100萬之間,他坦言,每年只要能有一兩個客戶,就已經能獲得很可觀的收益了。
大部分踐行“一人公司”的年輕人其實是歪歪這種,收入比在公司打工時要多,但遠稱不上暴富;在我們尚未接觸到的沉默踐行者中,像 Cellinlab 這樣還在探索、仍未盈利的人,無疑也有許多。
在瑪莎花11萬8報名的創業課程里,大約有20名同期生,一年過后,一半的人都消失了;兩年過后,真正靠著自己的雙手賺到錢、活下來的人數,一只手都數得過來。
“賺不到錢就會放棄”,“投入產出比不劃算就會放棄”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所以,付出了比在職場更多的精力,目前仍未實現收入同比例上漲的人,堅持是為了什么?
另一場追逐
每當遇到艱難時刻,歪歪的父親就會問她:你對這件事兒還有信心嗎?
歪歪回:有啊,怎么沒有了。
父親就會說:有信心就好,就能做。
軌道與曠野之間永遠有道無形圍墻,由“信”與“不信”彼此區隔。圍墻內的人因為不信,所以覺得圍墻外的人看到的新世界是“幻覺”;但對于圍墻外的人來說,恰恰是因為相信,才看到了真真實實的“曠野”。
《海上鋼琴師》里,1900在下船的舷梯中間停住,當他看到復雜的城市街景,還是回到了船上。他如此向朋友解釋:鋼琴只有88個按鍵,但你看過那些街道嗎,僅僅是街道就有上千條,該怎么選擇其中的一條路來走?
能夠接納“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追求”,是“曠野”給予人生的包容,可如果放棄“軌道”所給予的人生指引,只有堅定知道自己想走哪條路的人,才不會迷失,或是回頭。
在“一人公司”這種形態的“曠野”里,有些人追逐的仍舊是名利、金錢為自己帶來的安全感,有些人追逐的是“純粹做事的感覺”。無論是哪種,最終似乎都會收束回對于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探索。
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瑪莎,談吐幽默,金句頻出。
但她說自己以前是個十分靦腆的女孩兒,跟男生說話會臉紅,遇到事情會躲在家人的背后,不敢自己上前一步。直到父親去世,身體不好的母親需要照顧,她只能收起自己的情緒,一邊學習心理學,一邊安慰自己的母親。
畢業后,她努力抓住每一個機會,在北京工作、扎下根,一步步做到設計總監。
對于家人的看重以及攀登職場階梯的過往,給瑪莎留下的印記是,離開職場第一年,她就給自己定下了營收目標,不低全職工作的年收入。
這是她借以彰顯自身能力與價值的憑證,當這個目標已經實現,現在,她的動力變成了“幫助更多求職者”。
客戶離開、收入不穩時,歪歪也曾想過回到職場,她甚至已經通過了某大廠的面試,但還是放棄了。雖然她一開始笑著打趣“出來得久了就回不去了,不想坐班”,實際上她是不想背離自己希望“專注做內容”的初衷。
LK 曾親身經歷“大眾創業,萬眾創新”的時代,那是一段熱火朝天的日子,眼里看到的、耳邊聽到的都是誰創業了,誰融資了。大三下學期,他就跟同學在學校后面租了間房子,做創業。
盈利模式沒跑通,創業失敗后,曾經的伙伴有的去留學,有的回家當公務員,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是能閑下來的人。
“喜歡創造一個東西的感覺,這是不受控制的事情,在過程中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變化?!彪m然目前沒有融資的打算,但他覺得“一人公司”不是自己認為的常態,他仍期待著產品及商業模式成熟后的擴張時刻。
傳統職場的路徑中止了,但對于人生價值的另一場追逐不會隨之停下。
當離開了平臺、組織、公司,個體的肩膀上承擔了更多的職責與風險,那未必不是一個更殘酷的世界。
瑪莎搖了搖頭,“這不殘酷,這多刺激啊。”